|
云看看在线看最火影视 https://www.yunkk.cc 点击进入“凤凰网指数-影剧综榜单”查看最新榜单! 文/曾于里 5月20日就要来了。这是电影市场近年兴起的档期,常有爱情电影上映。 但今年的“520”,《暗恋·橘生淮南》《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》等卖相尚可的爱情片纷纷撤档。 从清明档、五一档到现在的“520档”,电影市场萧条许久。 但“520”仍有爱情电影上映,去年的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《白蛇传·情》被拿来重映。 电影业的现状,倒是当前文娱领域的一个缩影:没有新的东西,只能把旧东西拿来填充。 当前文娱领域正刮起“复古风”:受众对新的东西失去兴趣、或者压根就没有新的东西,大家纷纷在老片、老剧、老歌、老梗里寻求慰藉。 怀旧复古风,与疫情影响下人们对“确定性”的渴求有关。但它也折射了创作者对现实表达的失语。 01 受众:急于抓住一点确定性 电视剧领域,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爆款了。 上一部爆款《人世间》,多少也带有怀旧色彩,追忆的是往昔峥嵘岁月。与之相对的,一些老剧反而时不时就登上热搜。 譬如《甄嬛传》,催生了浩浩荡荡的“甄学家”,他们孜孜不倦地考察着剧中的细节,每有新的“知识点”出现,就能登上热搜。 根据云合数据,2022年第一季度新剧表现平庸,老剧(播出超过一年)却彰显出强劲生命力。 老剧有效播放414亿,同比上涨4.3%,在整个剧集大盘中的有效播放占比达54%,同比上涨7个百分点,片库内容相对价值持续提升。 电影领域,在反复不定的疫情下,影院开开停停。新片欠奉,老片重映、新片延长密钥成为新常态。 综艺领域,大阵仗的真人秀已经调动不起观众的兴奋感。 今年迄今,口碑最好的一档内娱真人秀,反而是小成本、也没怎么宣发的《欢迎来到蘑菇屋》。 第一批入驻的嘉宾,是2007年《快乐男声》13强里的陈楚生、苏醒、陆虎、王栎鑫、王铮亮、张远,可以称呼他们为“0713”组合。 他们自在舒服的相处,以及一首首藏在记忆深处的老歌,将观众带到2007年那个青涩但无忧无虑的夏天。 《声生不息》虽然带有很强的任务属性——香港回归25周年的献礼节目,但一向擅长做综艺的湖南卫视也敏锐找到“怀旧”切入点。 林子祥、李克勤、叶蒨文、杨千嬅、李玟,以及《遥远的她》《祝福》《大地》《情人》《来生缘》《花火》《我要你的爱》等歌曲,简直就是为80后量身定做。 看老片、追老剧、听老歌,甚至连梗都是“老”的。 10年前,斯琴高娃与袁立在采访中的“羊胎素梗”被重新翻出来,并在短视频平台上引发二次创作潮。 海清的《心居》热播时,2013年快男三强争夺战上,她公开为欧豪“拉票”的现场视频也被重新翻出来。 她握拳拜托评委,并走下V神台,单脚跪在欧豪面前,右手抚胸说:“刚才我是V神,现在你是我的神。”这一幕,谁看谁尴尬。 而此次疫情让刘畊宏意外爆红,网友们纷纷考古他的过去,绕不过去的依然是他与周杰伦的友谊,以及我们追台综的往事…… 文娱领域的这一“复古潮”,不免让人追问:怎么观众纷纷怀旧了?怎么纷纷在追忆“过去”、活在“过去”? 从心理学层面看,怀旧之所以产生,往往在于心理危机、身份认同危机。 在恐惧、不确定、焦虑的环境中,人们便倾向于怀旧,“重新体验过去生活的片段,以增加对现有环境的适应能力,并协助达到自我完整的目标”。 具体言之,这与疫情之下的全民艰难,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忧虑有关。 张爱玲曾经很精准地描绘了这种“末世”心理:“房子可以毁掉,钱转眼可以成废纸,人可以死,自己更是朝不保暮。像唐诗上的‘凄凄去亲爱,泛泛人烟雾’,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。人们受不了这个,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……” 什么东西是实在的?除了如张爱玲所言的“从柴米油盐、肥皂、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”外,还有“过去的东西”。 正因为“过去”,所以我们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,清楚故事的走向,我们知道谁是坏人,知道恶有恶报,我们不必为主人公的命运牵肠挂肚,只需要顺着情节看下去,舒适、稳妥、安全,甚至还能获得一点难得的快乐。 在不确定的时代,过去的东西提供了微茫的确定性。 这聊胜于无的确定性,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相信:所有故事会迎来它们的结局,我们必须捱过当下,捱过去,胜利也许就在前方,今天痛苦的一切都会付诸笑谈。 02 创作者:对现实的“失语” 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,观众沉浸在过去的故事里,恰恰也说明,当下的创作者,已经失去了表达现在、介入现在、引导情绪、创造流行的能力。 这的确是全球文娱领域创作的普遍特征:在资本、算法、IP时代,整个创作生态愈发平庸、保守。 就连流行文化的桥头堡好莱坞,亦是如此。 回想一下,从去年到今年,好莱坞几部火爆全球的电影,从《蜘蛛侠3:英雄无归》到《新蝙蝠侠》再到《奇异博士2》,哪一部不是IP或续集? 国内流行翻拍,好莱坞也很流行。 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《健听女孩》,翻拍自《贝利叶一家》。上周末在北美开画的《凶火》,就是老片翻拍——老片本身也挺平庸。 虽然票房扑街了,但《四个毕业生》《致命诱惑》《梦幻之地》《闪电舞》《异形》的翻拍,已被好莱坞制作方提上日程。 而前段时间,流媒体巨头Netflix的股价一跌再跌,已经跌到市值最高峰时期的三分之一。 资本市场不看好Netflix,除了流媒体惨烈的竞争以外,也在于不看好Netflix那种“算法电影”“算法剧集”…… 大数据做的东西,只有迎合,没有引领,很难具备个性与创造性。 当前内娱一些弊病,与好莱坞倒是如出一辙。譬如对IP的追捧,翻拍与重拍潮,平台算法主导创作…… 可内娱又有独属于它的困境。 好莱坞再怎么不济,它都有自由开放的创作氛围;几大制作公司不行了,但一些独立的制作公司还是一直在推出有个性的作品。 如果说好莱坞是欧美流行领域的商业代表,戛纳电影节就是艺术指标。虽然也受到疫情影响,但戛纳电影节已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。 不久前戛纳公布了今年主竞赛名单,世界影坛依然生机勃勃,大卫·柯南伯格、达内兄弟、朴赞郁、是枝裕和、克里斯蒂安·蒙吉、鲁本·奥斯特伦德等人的新片均在名单中。 而华语电影已经连续两年缺席主竞赛单元了。哪怕是世界都在退步,我们也退步得更快。 是我们创作者缺乏把握现实的能力吗? 不见得。曾几何时,华语电影也能叱咤三大电影节。 这种表达的失语,更多来自于外力的压力。有系统的审查,甚至观众也会自行审查。 批判现实主义,本是介入现实的常见创作手法,但如今它显得很“危险”。 要么过审难、未能顺利面世,给投资方带来风险;要么面世后要遭遇舆论批判,影响市场前景。 譬如去年的《雄狮少年》,可以看到当下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轻人的生存镜像,但它却因为所谓的“眯眯眼”遭到抵制。 假设有对现实的表达,也愈发呈现出同一种步调、同一种声音——只能记录更光明的一面,如果聚焦的是时代里一粒灰下的小人物,可能会被视为“居心叵测”。 所以我们发现,如今的影视剧市场,更多是关注过去——古装言情、古装历史、民国年代。如果聚焦当下,也主要是都市爱情、都市职场、批判有限的悬疑,以及主旋律。 比如,虽然有扫黑除恶的大尺度情节,但《对决》也要念大段大段的官方文件。 虽然有提及疫情下的困难,但从《最美逆行者》《在一起》到《穿过寒冬拥抱你》,基调也只能是温暖的、治愈的、歌颂的。 夹缝中的创作者选择空间有限,他们只能屈从于现实压力,或对现实困境视而不见,或对现实进行主旋律表达。 这与观众所处的现实产生严重的错位与偏差,观众无法从这样的表达获得共鸣、抵达反思、看见希望,也就逐渐对文娱领域的现实表达失去兴趣。 于是只能活在“过去”,触摸旧时光的余辉,才能获得片刻快乐,才能释放那么一点愤怒,才能浇心中之块垒。 更多一手新闻,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订阅Ifeng电影。想看深度报道,请微信搜索“Ifeng电影”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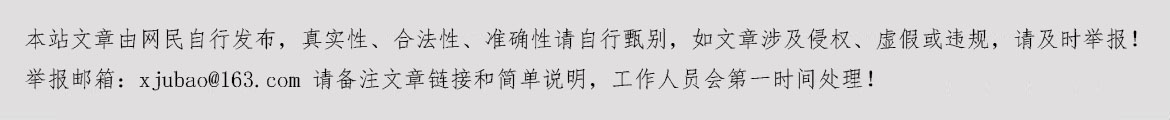
|